男女主角分别是昭宁林昭宁的其他类型小说《吾将以身祭天,惟愿卿世世长安。前文+后续》,由网络作家“吊打白骨精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柔,不过是铸鼎匠在宿命前,偷来的片刻时光。“我该怎么回答你?”她对着鼎腹低语,笔尖悬在朱砂上方,迟迟落不下去。远处传来打更的电子钟响,已是子时。青铜鼎沉默着,只有她的银铃在寂静中轻轻摇晃,发出三千年都没变过的清响。第二章:铸鼎人言寒露后的文物医院总带着潮气,昭宁的指尖在鼎腹上停留了整整十分钟。裴溯的问题像块烧红的炭,烙在青铜表面:“你所在的时代,可还有‘人祭’?”最后那个“祭”字的末笔拖出半道血痕,像是笔尖划破了皮肤。“裴溯,”她声音发颤,狼毫笔在瓷碟里搅出凌乱的朱砂,“什么是人祭?和你的铸鼎有关吗?”墨迹在鼎内晕开,许久才浮出几行字,笔画比往常粗重,像握笔的手在用力:“王室铸祈雨鼎,需以铸鼎师血祭于天。鼎成之日,我便要跳进铸炉。”...
《吾将以身祭天,惟愿卿世世长安。前文+后续》精彩片段
柔,不过是铸鼎匠在宿命前,偷来的片刻时光。
“我该怎么回答你?”
她对着鼎腹低语,笔尖悬在朱砂上方,迟迟落不下去。
远处传来打更的电子钟响,已是子时。
青铜鼎沉默着,只有她的银铃在寂静中轻轻摇晃,发出三千年都没变过的清响。
第二章:铸鼎人言寒露后的文物医院总带着潮气,昭宁的指尖在鼎腹上停留了整整十分钟。
裴溯的问题像块烧红的炭,烙在青铜表面:“你所在的时代,可还有‘人祭’?”
最后那个“祭”字的末笔拖出半道血痕,像是笔尖划破了皮肤。
“裴溯,”她声音发颤,狼毫笔在瓷碟里搅出凌乱的朱砂,“什么是人祭?
和你的铸鼎有关吗?”
墨迹在鼎内晕开,许久才浮出几行字,笔画比往常粗重,像握笔的手在用力:“王室铸祈雨鼎,需以铸鼎师血祭于天。
鼎成之日,我便要跳进铸炉。”
昭宁的笔“啪”地掉进碟子里,朱砂溅在白大褂上,像朵开败的梅。
她踉跄着扶住修复台,看见鼎腹内侧隐约映出自己的倒影,和千年前那个跪在铸炉前的身影重叠。
“为什么?”
她指尖抠进鼎沿的纹路,“就因为你是铸鼎师,就要拿命换一场雨?”
回信很慢,每个字都带着停顿:“七岁被选入王室铸坊,师父说,我们的骨血天生属于鼎。
十七岁那年,他把我推进燃烧的火坑,说这是‘祭鼎人的试炼’。”
昭宁看见“火坑”二字周围,有极细的凹痕,像是笔尖反复戳刺铜面留下的。
她忽然想起裴溯信里提过的“骨血刻纹”,原来每一道鼎纹,都是铸鼎师用伤痛刻下的符咒。
喉间泛起苦味,她摸出手机,翻到西周祭祀的资料——人祭记载多是“献牲于神”,却没提过铸鼎师的宿命。
“现代不会这样了,”她急切地回信,“你可以逃,法律会保护你,没有人有资格夺走你的生命!”
墨迹刚干,鼎内突然浮出一串歪斜的划痕,像是被利器划过。
昭宁惊觉那是裴溯的字迹,却破碎得无法辨认,最后只余下半句:“逃?
邑落的百姓会被旱灾吞掉……”沉默在室内蔓延。
昭宁盯着那些断裂的笔画,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话有多天真——三千年的风沙里,“个人”的生死从来都轻如鼎上
“宁”字和工牌编号,仿佛他在铸鼎时就已算准,三千年后会有双手为他拼接这些碎光。
当最后一片鼎足归位,她忽然看见残片交界处浮出半行小字,是裴溯的字迹,比任何时候都清晰:“别怕,我的血在鼎纹里,永远护着你。”
暴雨冲刷着医院的外墙,昭宁的银铃在残片旁微微震动,发出比三千年更轻的响。
她终于明白,那些藏在鼎腹里的对话,从来不是偶然的通神,而是一个铸鼎匠在知道必死的命运后,用骨血为心上人凿开的、能看见未来的裂缝。
而此刻,裂缝正在闭合。
残片上的朱砂字渐渐淡去,唯有“世世长安”四字,像嵌进青铜的赤金,在她流泪的视线里,永远凝固成春天的形状。
第五章:千劫烬余消毒水的气味还粘在袖口,昭宁跪在文物医院的修复台前,指尖捏着最小的鼎腹残片。
台灯的冷光下,十七块碎铜片像散落的星辰,每道裂痕都映着她红肿的眼。
“这里应该有通神纹……”她声音沙哑,镊子夹起刻着“宁”字的残片,发现笔画边缘泛着极细的金箔纹——那是裴溯混着血与青铜熔液刻下的,三千年后仍在微微发烫。
当最后一片鼎足归位,整尊鼎突然发出极轻的“嗡鸣”,仿佛三千年的时光在裂痕间轻轻叹息。
展柜的玻璃映出她苍白的脸。
昭宁看见鼎腹内侧的空白处,渐渐浮现出淡金色的纹路——不是西周的云雷纹,而是某种螺旋状的轨迹,像时光的河流在青铜上蜿蜒。
这是裴溯从未提过的“通神纹”,原来他早在铸鼎时,就用自己的血为媒介,在鼎腹凿开了连接未来的裂缝。
“你说过铸鼎师的骨血属于鼎,”她指尖抚过螺旋纹,忽然想起裴溯信里的“火坑试炼”,“原来你早把自己的命,炼成了这道能遇见我的纹。”
资料室的古籍在深夜翻开。
昭宁的手指划过《西周祭器志》泛黄的纸页,在“祈雨鼎”条目下方,发现一行被虫蛀的小字:“铸师裴溯,于鼎成前夜书竹简,藏于鼎腹,言‘以血为墨,通三千年光阴’。”
墨迹边缘有暗红渗染,与残片上的朱砂字如出一辙。
她终于明白那些回信为何总带着炭火味、桑椹香、甚至偶尔的血迹——裴溯每次刻字,都是从正
序章:青铜凝霜2025年4月的夜风裹着春寒,从故宫琉璃瓦的缝隙间漏进文物医院。
林昭宁指尖抵着青铜鼎腹,竹笔上的朱砂在LED冷光下泛着暗红,像凝固的血。
这尊西周祈雨鼎送来时满身铜锈,鼎腹内壁的铭文被绿锈啃得支离破碎,唯有“祈雨”二字如刀刻般清晰。
她已经盯着这处空白看了三天——本该布满铭文的区域,却平滑得反常,像被人刻意留白。
“要是能听听千年前的雨声就好了。”
她白天擦着鼎沿时曾随口念叨,此刻加班到深夜,手指突然触到一片湿润。
青铜表面凝着一层薄霜,像被千年时光镀了层冰。
昭宁蹙眉用棉签擦拭,却见霜气退去的地方,竟浮出一行古篆,笔画边缘还带着未干的墨痕:“卯时三刻,雨落如注,陶埙声自西南来。”
竹笔“当啷”掉在工作台上。
她猛地站起身,椅子腿在地面划出刺耳声响。
空调的嗡鸣突然变得格外清晰,窗外的月亮正透过百叶窗,在鼎身上投下斑驳的格状光影。
“不可能……”昭宁指尖发颤,抽出白手套反复擦拭鼎腹。
墨迹却稳稳嵌在铜纹里,每个笔画都带着西周金文特有的弧度,仿佛千年前就刻在那里。
她忽然想起下午的场景:阳光斜照进窗户,她对着鼎腹呵气,白雾在“祈雨”二字旁聚成小水滴,那时她确实说了那句话。
可现在——“是你在回答我?”
她屏住呼吸,贴近鼎腹,鼻尖几乎触到冰冷的铜面。
没有回应,只有空调外机的震动声撞在寂静里。
昭宁咬了咬唇,从工具盒里翻出最细的狼毫笔。
朱砂在瓷碟里晃出细碎涟漪,她屏住呼吸,在空白处落下第一笔:“你是谁?”
笔尖触到铜面的瞬间,她忽然觉得掌心发麻,像有电流顺着笔杆爬进血管。
墨迹在鼎腹上晕开,却比寻常朱砂更浓,暗红中透着金箔般的微光。
收拾工具时,她忍不住又回头看了眼鼎。
月光给青铜镀上银边,那行新写的字静静躺在“祈雨”下方,像沉睡千年的人终于睁开了眼。
凌晨三点,昭宁躺在值班室的小床上辗转难眠。
手机屏幕亮了又暗,故宫的监控系统在床头闪着幽蓝的光。
她数着窗外的鸟鸣,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,才迷迷糊糊闭上眼。
再睁
少见的轻快:“照着你的铃刻的,挂在铸模上,风过时会响。”
秋风吹落第一片银杏叶时,昭宁开始向裴溯描述现代生活。
她画地铁线路图,用便签纸写下“手机”的功能,甚至把自己的工牌照片打印成微缩版,塞进鼎腹。
裴溯的问题越来越多:“铁制的车能在地下跑?
比马拉的车快吗?”
“展柜的玻璃为何不会碎?
是不是比青铜还坚固?”
但他很少提自己。
直到那天,昭宁在信里说起文物修复的意义:“我们修补的不仅是文物,更是千年前匠人的心意。”
裴溯的回信突然慢了五天,字迹也变得沉重:“若你知道,这鼎的每道纹都是用铸鼎师的骨血刻成,还会觉得心意珍贵吗?”
昭宁握着笔的手顿住了。
窗外的银杏叶正扑簌簌落下,像极了信里说的“桑林落叶”。
她忽然意识到,那些偶尔出现在信里的铜渣、沙粒、草木香,或许都是裴溯在铸炉旁、在桑林下、在即将完成的鼎身侧,用沾满铜锈的手写下的。
“裴溯,” 她盯着鼎腹,轻声说,“你铸的鼎,会被现代人记住的。
你的名字,也会。”
墨迹在鼎内晕开,她不知道三千年前的人能否听见,但指尖触到的青铜,似乎比往常多了丝温度。
霜降前夜,裴溯的信里突然出现个突兀的问题:“你所在的时代,可还有‘人祭’?”
字迹歪斜,最后一笔拖出长长的划痕,像笔尖在铜面上打滑。
昭宁盯着那个“祭”字,发现笔画里混着暗红,像是渗了血。
她猛地站起身,银铃手链撞在修复台上发出脆响。
窗外的月亮被乌云遮住一半,青铜鼎在阴影里泛着冷光,那些曾让她觉得温柔的墨痕,此刻突然蒙上了一层寒意。
“人祭?”
她喃喃重复,忽然想起西周史料里的只言片语。
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银铃,铃身的云雷纹硌着掌心——那是裴溯刻在小铃上的纹路,也是铸在祈雨鼎上的纹路。
原来从第一次通信起,他就在试探,在隐忍,在等待她发现真相的那天。
昭宁取出笔记本,翻到记满裴溯字迹的那页。
三个月来的对话像青铜锈般层层叠叠,她忽然发现,所有关于铸鼎的细节,都绕不开“火候祭纹骨血”,而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温
的她怎么也想不到,三千年的距离,最终会化作鼎纹里的一滴血、银铃中的一道光。
笔尖刚触到鼎腹,银铃突然发出清越的响。
昭宁屏住呼吸,看见熟悉的古篆墨迹在铜面浮现,虽然只有短短三个字,却让她眼眶瞬间发热:“霜雪至。”
墨迹边缘带着极细的金砂,是裴溯独有的笔触。
她颤抖着回信:“今年的初雪,会落在你刻的银杏叶上吗?”
狼毫在“你”字收笔处顿了顿,补了句当年没说出口的话:“我数过了,桑椹干的味道,和你留在鼎纹里的血,一样甜。”
等待回信的时间里,昭宁摸着鼎足的凹槽,那里藏着她的工牌编号,还有裴溯刻的微型银铃。
她忽然听见远处传来打更的电子钟响,是故宫新换的报时系统,却意外地,像极了三千年前邑落的铜钟声。
“来了。”
当鼎内浮现“安”字时,昭宁笑了。
这个字比任何时候都工整,笔画间却藏着不易察觉的颤笔——就像裴溯在铸炉旁,用最后力气刻下的、跨越千年的“平安”。
展柜玻璃上凝着薄霜,昭宁呵气擦出小块透明,看见自己的倒影与鼎纹里的云雷纹重叠。
腕间银铃轻晃,惊落一片银杏叶,恰好覆在“世世长安”的“世”字上,像给三千年的时光,添了片会呼吸的金箔。
她知道,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,终将随着青铜的氧化慢慢淡去。
但那些嵌在鼎纹里的血与墨,那些藏在银铃中的光与响,早已让两个相隔三千年的灵魂,在文物的年轮里,结成了比铭文更不朽的契约。
锁门前,昭宁最后看了眼展柜。
祈雨鼎在月光下静静矗立,鼎腹内侧的墨迹虽已消散,却有无数细小的光点在裂缝间流转,像裴溯当年偷藏的、属于人间的星光。
“晚安,裴溯。”
她轻声说,银铃随着转身的动作发出细碎的响,“明天,我会带新的桑椹干来,就放在你刻的‘宁’字旁边——这次,换我等你回信。”
展厅的灯次第熄灭,唯有祈雨鼎上方的长明灯仍亮着。
在无人的深夜里,青铜表面偶尔闪过极淡的朱砂色,像有人在时光的另一端,轻轻应了声“好”。
而那串陪着昭宁走过三千年的银铃,正随着穿堂风,哼着比任何祭文都温柔的、永不褪色的歌谣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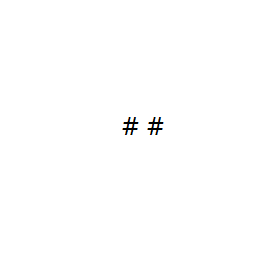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